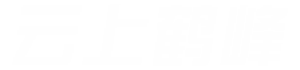жҙһжәӘеқӘпјҢжҳҜдёҖеә§зҫҺдёҪиҖҢе®Ғйқҷзҡ„еұұжқ‘пјҢж ‘жңЁз№ҒиҢӮпјҢйёҹйёЈеұұе№ҪпјҢдә‘йӣҫзјӯз»•пјҢиҝңзҰ»еҳҲжқӮе’Ңе–§еҡЈпјҢдёәйўҗе…»иә«еҝғзҡ„д№җеӣӯгҖӮ
йӮЈйҮҢзҡ„з”°еӣӯйЈҺжғ…пјҢжҖ»жҳҜж·ұж·ұжүҺж №еңЁжҲ‘зҡ„и®°еҝҶйҮҢгҖӮд»ҺжҙһжәӘеқӘиө°еҮәеҺ»пјҢеңЁеӨ–жү“жӢјзҡ„жёёеӯҗпјҢж·ұжғ…ең°жҢӮеҝөйӮЈзүҮеңҹең°пјҢйӮЈж–№еұұж°ҙгҖӮиө°еңЁејӮд№Ўзҡ„еңҹең°дёҠпјҢжңӣзқҖејӮд№ЎеӨ©з©әдёҠзҡ„зҷҪдә‘пјҢжқҺзҷҪзҡ„иҜ—еҸҘвҖңжө®дә‘жёёеӯҗж„ҸпјҢиҗҪж—Ҙж•…дәәжғ…вҖқжҖ»еңЁеҝғдёӯе”ұиө·пјҢйҳөйҳөд№Ўж„Ғзјӯз»•еҝғй—ҙпјҢжҢҘд№ӢдёҚеҺ»гҖӮ
жҙһжәӘеқӘеңҹең°дёҠжӣҫеұ…дҪҸиҝҮж—Ұ姓пјҢжҪҳ姓пјҢйӣ·е§“пјҢ尹姓пјҢйҷҲ姓пјҢзҪ—姓пјҢ黄姓пјҢеӯҷ姓пјҢдҫҜ姓гҖӮиҝҷдәӣ姓ж°ҸеҸҜиғҪжҳҜеҮ зҷҫе№ҙеүҚзҡ„еҺҹеұ…ж°‘пјҢеҫҲеӨҡең°еҗҚе°ұжҳҜд»Ҙ他们зҡ„姓ж°Ҹе‘ҪеҗҚзҡ„гҖӮиҖҢд»Ҡиҝҷдәӣ姓ж°ҸеңЁжҙһжәӘеқӘдёҚеӨҚеұ…дҪҸпјҢжҲ–и®ёиҝҷдәӣ姓ж°Ҹи—ҸзқҖеҜҶз ҒпјҢи—ҸзқҖз”ҹеҠЁзҡ„еҺҶеҸІж•…дәӢпјҢд№ҹжңӘеҸҜзҹҘгҖӮзҺ°еңЁеұ…дҪҸзқҖе»–ж°ҸпјҢз”°ж°ҸпјҢи°·ж°ҸпјҢйӮ“ж°ҸпјҢиӮ–ж°ҸпјҢй«ҳж°ҸпјҢжқЁж°ҸпјҢе‘Ёж°ҸпјҢзҺӢж°ҸпјҢйҷ¶ж°ҸгҖӮ
жҙһжәӘеқӘеҢ—еұұеҗҺйқўжңүдёҖдёӘең°ж–№еҸ«еңҹе ЎгҖӮеҺ»еңҹе Ўзҡ„еұұи·ҜжңүдёүжқЎпјҢиҘҝи·Ҝд»ҺжңҲдә®еһӯпјҢдёӯи·Ҝд»ҺиҖҒйёҰеҜЁпјҢдёңи·Ҝд»Һж°ҙдә•иәәгҖӮдёӯи·Ҝд»ҺжҲ‘иҖҒ家еұӢеҗҺпјҢжІҝзқҖдёӣжһ—йҮҢеҙҺеІ–зҡ„е°Ҹи·ҜпјҢзҷ»дёҠеұұйЎ¶пјҢзҝ»иҝҮеұұеһӯпјҢжЁӘзқҖеұұи·Ҝз»ҸиҝҮдёҖдёӘеҸ«иҖҒйёҰеҜЁ(жҲ–еҸ«иҖҒеЁғеҜЁпјҢеҸҜиғҪд№ҢйёҰеӨҡпјҢж•…еҗҚ)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ҶҚжІҝзқҖйҷЎеіӯзҡ„еұұи·ҜдёӢиЎҢеҲ°еұұи…°зј“еҶІең°еёҰпјҢйӮЈйҮҢжңүеҮ еҚҒдә©еқЎең°пјҢеқЎең°е·ҰеҸіеҗ„жңүдёҖдәӣе°ҸеІӯи„Ҡе’ҢеұұејҜпјҢйӮЈйҮҢе°ұеҸ«еңҹе ЎгҖӮ
еңҹе ЎдёӢйқўжҳҜеҘ”и…ҫдёҚжҒҜзҡ„е®ҳеә„жІіпјҢеҚіжҳҜиҠӯи•үжІідёҖзә§еққж°ҙеә“дёҠжёёе°ҫж°ҙжІіж®өгҖӮйӮЈйҮҢзҡ„ж ‘жһ—йҮҢжӣҫжңүиҖҒиҷҺгҖҒзӢ—зҶҠпјҢйҮҺзҢӘпјҢйәӮеӯҗпјҢзҚҗеӯҗпјҢй”ҰйёЎпјҢйҮҺйёЎеҮәжІЎпјӣжІійҮҢжӣҫжңүеЁғеЁғйұјпјҢжҙӢйұјпјҢеңҹйұјпјҢзЈ…зЈ…зӯүж°ҙз”ҹзү©е¬үжҲҸгҖӮ他们жҳҜе®ҳеә„жІіи°·зҡ„зІҫзҒөпјҢеӣ жңүдәҶиҝҷдәӣйІңжҙ»зҡ„еӯҳеңЁпјҢжӣҫз»Ҹзҡ„е®ҳеә„жІіжҳҜдёҖжқЎе……ж»ЎйҮҺжҖ§еҺҹе§Ӣзҡ„жІіжөҒпјҢдёӨеІёж ‘жңЁжҗӯ蓬пјҢйҒ®еӨ©и”Ҫж—ҘгҖӮжё…жҫҲзҡ„жІіж°ҙеңЁеұұи°·е“—е“—жөҒж·ҢпјҢеҘ”жөҒеЈ°еӣһиҚЎеұұи°·пјҢж—¶еёёдә‘йӣҫзјҘзјҲпјҢж°”иұЎдёҮеҚғгҖӮеңҹе ЎеҜ№йқўжҳҜдёӯиҗҘжҹіжқ‘пјҢдёҺеңҹе Ўйҡ”жІізӣёжңӣгҖӮеңҹе ЎйӮЈйҮҢжңүдёғе…«дә©еӨ§е…ңеӯҗиҢ¶ж ‘пјҢдёҠзҷҫе№ҙзҡ„ж ‘йҫ„пјҢи—ҸеңЁдёӣжһ—йҮҢпјҢеҗёеӨ©ең°зІҫеҚҺпјҢйӨҗйЈҺжІҗйӣЁпјҢеҺҹе§ӢйҮҺз”ҹпјҢдёәж— д»·д№Ӣе®қгҖӮжҲ‘дёҖзӣҙжғіеҺ»еңҹе ЎжҺўйҷ©пјҢзҺ°еңЁеҺ»еңҹе Ўзҡ„еұұи·Ҝе·Із»ҸиҚ’иҠңпјҢй•ҝж»ЎиҚүжңЁпјҢйҡҗе…Ҙж ‘жһ—д№ӢдёӯгҖӮ
иҜқиҜҙи§Јж”ҫеүҚпјҢеңҹе Ўйҷ„иҝ‘дҪҸзқҖдёүжҲ·дәә家пјҢдёҖжҲ·еә·е§“пјҢдёӨжҲ·жқЁе§“гҖӮеә·е§“еұӢйҮҢзҡ„зҲ·зҲ·еҸ«иҙӨзҲ·пјҢе©Ҷе©Ҷ姓и’ӢпјҢжңүдёӨдёӘеҘіе„ҝгҖӮеӨ§еҘіе„ҝеҗҚе…ғиӢұпјҢ20еӨҡеІҒпјҢжӢӣзҡ„дёҠй—ЁеҘіе©ҝпјҢ姓黄пјӣе°ҸеҘіе„ҝеҗҚе…ғз”ҹпјҢ18еІҒпјҢеҫ…еӯ—й—әдёӯгҖӮжқЁе§“еұӢйҮҢзҡ„зҲ·зҲ·еҸ«з»ӘзҲ·е’Ңе®қзҲ·пјҢз»ӘзҲ·е’Ңе®қзҲ·жҳҜеҸ”дјҜе…„ејҹгҖӮз»ӘзҲ·е®¶зҡ„е©Ҷе©Ҷ姓еҗҙпјҢе®қзҲ·е®¶зҡ„е©Ҷе©Ҷе§“еј гҖӮйӮЈж—¶пјҢз»ӘзҲ·е’Ңе®қзҲ·е®¶зҡ„еӯҗеҘійғҪиҝҳе№ҙе№јгҖӮз»ӘзҲ·е’ҢиҙӨзҲ·дёӨ家зҡ„жҲҝеұӢзӣёйҡ”дёҚиҝңпјҢд№ҹе°ұдёӨдёүйҮҢи·ҜзЁӢпјҢдёӨеұӢд№Ӣй—ҙйҡ”дёӘе°ҸеІӯи„ҠпјҢй«ҳеЈ°еҗҶе–қпјҢеҸҜд»Ҙдә’зӣёе–ҠиҜқгҖӮиҙӨзҲ·зҡ„еұӢеңЁз»ӘзҲ·зҡ„дёңиҫ№пјҢйқ 马зҺӢжҙһж–№еҗ‘гҖӮе®қзҲ·зҡ„еұӢйҡ”еҫ—иҝңдёҖдәӣпјҢеңЁз»ӘзҲ·зҡ„иҘҝиҫ№пјҢйқ иғҢејҜж–№еҗ‘пјҢдёҺз»ӘзҲ·зҡ„жҲҝеұӢйҡ”еҮ дёӘе°ҸеұұејҜе’Ңе°ҸеұұеІӯгҖӮ
и§Јж”ҫйӮЈдёҖе№ҙпјҢз»ӘзҲ·йў„зәҰжқЁе®¶еһӯзҡ„敬зҲ·еҲ°д»–家иҝҮжңҲеҚҠпјҢд»–дҝ©жҳҜеҘҪе“Ҙ们пјҢжҖ»жңүиҜҙдёҚе®Ңзҡ„иҜқпјҢж—¶еёёеңЁдёҖиө·еҜ№й…’еҪ“жӯҢпјҢдёҫжқҜйӮҖжңҲгҖӮ敬зҲ·жҸҗеүҚдёҖеӨ©пјҢдәҺдёғжңҲеҚҒдәҢеҮәеҸ‘еүҚеҫҖеңҹе ЎгҖӮиғҢзҜ“йҮҢиғҢдёҖеқ—и…ҠиӮү пјҢдёӨж–Өй…’пјҢиәәиҝҮж–°и·ҜжІҹпјҢи·ҜиҝҮйә»еқ‘пјҢзҲ¬дёҠйҷҲ家еҜЁпјҢзҝ»иҝҮж°ҙдә•иәәпјҢз»ҸиҝҮзҹ®зүҷеӯҗ пјҢдёӯеҚҲж—¶еҲҶжқҘеҲ°з»ӘзҲ·е®¶йҮҢгҖӮиЈ…зғҹзӯӣиҢ¶пјҢдёҖйҳөдәІзғӯжӢӣе‘јй—®еҖҷпјҢеҗҙе©Ҷе©ҶеңЁзҒ¶еұӢеҝҷиҝӣеҝҷеҮәпјҢеҝҷеүҚеҝҷеҗҺпјҢзғ§зҒ«з…®иӮүпјҢжҙ—иҸңеј„йҘӯгҖӮз»ӘзҲ·е’Ң敬зҲ·иЈ№зқҖеӨ§еҸ¶еӯҗеңҹзғҹпјҢеҗһдә‘еҗҗйӣҫпјҢеқҗеңЁе ӮеұӢжӢү家常пјҢз…ҪйҮҺзҷҪпјҢеҶ…е®№еӨ©еҚ—ең°еҢ—пјҢд№Ўжқ‘дәәзү©пјҢиә«иҫ№ж•…дәӢпјҢ家й•ҝйҮҢзҹӯгҖӮдәҢдёӨй…’дёӢиӮҡпјҢ敬зҲ·е’Ңз»ӘзҲ·и„ёдёҠеҫ®еҫ®жіӣзәўгҖӮеҗғе®ҢйҘӯпјҢе·ІжҳҜе…ӯдёғзӮ№пјҢеӨ©еңЁжү“йә»зңјпјҢдёӢзқҖе°ҸйӣЁпјҢ敬зҲ·е’Ңз»ӘзҲ·дёҖ家дәәеқҗеңЁе ӮеұӢпјҢеҖҹзқҖй…’еҠІж‘Ҷйҫҷй—ЁйҳөгҖӮ
жӯӨж—¶пјҢдёүдёӘдёӯзӯүдёӘеӨҙзҡ„еӨ–ең°дәәпјҢжӯЈиЎҢиүІеҢҶеҢҶиө°еңЁжҙһжәӘеқӘзҡ„и·ҜдёҠпјҢдёүдәәйғҪжңүжҳҫи‘—зҡ„ж Үи®°пјҢдёҖдёӘи„ёдёҠйқ’зӯӢзҲҶеҮәпјҢдёҖдёӘзңјзқӣйј“еҮәеҰӮйқ’иӣҷпјҢдёҖдёӘйј»еӯҗзјәдёҖе°Ҹеқ—пјҢе°ҸйӣЁжҡ®иүІдёӯпјҢжҜҸдәәиғҢдёӘжӨӯеңҶиғҢзҜ“(жқҘеҮӨе®ЈжҒ©е’Ңж№–еҚ—жңүиҝҷз§ҚиғҢзҜ“)пјҢж—¶дёҚж—¶дёңеј иҘҝжңӣпјҢжңқиӢҰз«№еһӯгҖҒжҪҳ家еұӢеңәж–№еҗ‘з–ҫиЎҢпјҢи¶ҠиҝҮзҢҙи„ҠејҜгҖҒж°ҙдә•иәәпјҢеӨ©еҝ«й»‘пјҢдёүдәәжҳҺжҳҫеҠ еҝ«и„ҡжӯҘпјҢжңқзҹ®зүҷеӯҗж–№еҗ‘еҘ”еҺ»гҖӮ
дёүдәәжІҝеҜ®з«№иҢ…иҚүи·Ҝе°Ҹи·‘иҮіиҙӨзҲ·еұӢиҫ№пјҢеӨ©е·Ій»‘пјҢеңЁеӨң幕дёӯеҜ№е‘Ёеӣҙең°еҪўзңӢдәҶзңӢпјҢйҷӨдәҶиҙӨзҲ·е®¶пјҢжІЎжңүзңӢеҲ°еӨҡдҪҷзҡ„з…ӨжІ№зҒҜдә®е…үгҖӮдёүдәәзӘғзӘғз§ҒиҜӯпјҢйј“зңјзқӣиҜҙ:д»ҠжҷҡеҸҜд»ҘеңЁжІійҮҢй’“еҲ°еӨ§йұјгҖӮ
вҖңиҖҒжқҝпјҢжҲ‘们и·ҜиҝҮиҝҷе„ҝпјҢжө‘иә«жү“ж№ҝе®ҢдәҶпјҢеӨ©д№ҹй»‘е“’пјҢжӯҮеҳҺйӣЁпјҢзғӨе“ҲиЎЈжңҚгҖӮвҖқвҖңеҘҪзҡ„пјҢеҘҪзҡ„пјҢиҝӣжқҘпјҢиҜ·еқҗгҖӮвҖқиҙӨзҲ·дёҖиҫ№жӢӣе‘јпјҢдёҖиҫ№жҗ¬жңЁжӨ…еӯҗгҖӮеңЁз…ӨжІ№зҒҜжҳҸжҡ—зҡ„е…үзәҝдёӯпјҢдёүдәәжҜ«дёҚе®ўж°”зҡ„иҝӣеҲ°еұӢйҮҢпјҢеқҗеңЁзҒ«зӮүеқ‘иҫ№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еҝҷзқҖжҗ¬жқҘжҹҙжһқпјҢжҠҠзҒ«зӮүеқ‘зҡ„зҒ«зғ§еҫ—ж—әж—әең°пјҢеӨ§зӮүеӨ§зҒ«ең°и®©дёүдәәзғӨзҒ«пјҢзғҳзғӨж№ҝиЎЈжңҚпјҢз ҙж—§зҡ„ж№ҝиЎЈжңҚзғӯж°”зӣҙеҫҖдёҠеҶ’пјҢеғҸзј•зј•иҪ»зғҹгҖӮиҙӨзҲ·е®ўж°”ең°з»ҷдёүдәәеҖ’ж°ҙжіЎиҢ¶е–қгҖӮеңЁжҹҙзҒ«еҸ‘еҮәзҡ„е…үдә®дёӯпјҢдёүдәәзҡ„е°Ҡе®№жҳҫеҫ—жё…жҷ°иө·жқҘпјҢе…ғиӢұе’Ңе…ғз”ҹжҳҺжҳҫж„ҹеҲ°дәҶдёҚе®үгҖӮ
вҖңдёүдҪҚе®ўдәәеҺ»е“ӘйҮҢ?иҝҷд№ҲжҷҡдәҶгҖӮвҖқиҙӨзҲ·й—®йҒ“гҖӮвҖңжҲ‘们еҺ»е®ЈжҒ©пјҢжҒ©ж–ҪпјҢи·ҜиҝҮиҝҷе„ҝпјҢеҜ№и·Ҝд№ҹдёҚзҶҹжӮүпјҢиҝ·и·ҜдәҶгҖӮвҖқйј“зңјзқӣзңјжү«зқҖеұӢеҶ…еӣӣи§’пјҢеӣһзӯ”йҒ“гҖӮвҖңд»Ҡе„ҝжҷҡдёҠеҲ°иҖҒжқҝиҝҷйҮҢеҖҹеҳҺжӯҮеӨ„пјҢи·ҹиҖҒжқҝжҠҠзӮ№зӣҳзј вҖқпјҢзјәйј»еӯҗжңқе ӮеұӢжңӣдәҶжңӣпјҢеӨ§еЈ°иҜҙйҒ“гҖӮвҖңжҲ–иҖ…е°ұдёҚзқЎпјҢеңЁиҖҒжқҝ家иәІйӣЁпјҢзғӨдёҖеӨңзҒ«д№ҹиЎҢвҖқпјҢйқ’зӯӢжҳӮзқҖеӨҙпјҢиҙӘе©Әең°жңӣзқҖеӨҙйЎ¶зӮ•жһ¶дёҠзҡ„еҮ еқ—иҖҒи…ҠиӮүпјҢиЎҘе……йҒ“гҖӮеҗ¬еҲ°дёүдәәиҝҷж ·иҜҙпјҢиҙӨзҲ·е’Ңи’Ӣе©Ҷе©ҶйқўйңІйҡҫиүІ пјҢеҸҲдёҚеҘҪжӢ’з»қпјҢиҝҳжңүдёҖдёқйҡҗйҡҗзҡ„жӢ…еҝ§гҖӮ
иҜҙжқҘдәӢжңүеҮ‘е·§пјҢйӮЈеӨ©е…ғиӢұз”·е®ўеҮәдәҶиҝңй—ЁпјҢжІЎеӣһ家пјҢеҲҡеҘҪеҸҜд»Ҙи…ҫеҮәдёҖдёӘй“әпјҢ他们дёүдәәд№ҹеҸҜд»Ҙе°Ҷе°ұдёҖеӨңпјҢеҸӘеҘҪеӢүејәзӯ”еә”гҖӮ
зәҰж‘ёд№қзӮ№е·ҰеҸі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еӮ¬дҝғе…ғиӢұгҖҒе…ғз”ҹе§җеҰ№жҙ—и„ҡдәҶж—©зӮ№дј‘жҒҜпјҢеңЁе ӮеұӢжҙ—и„ҡж—¶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йҷ„иҖіиҪ»еЈ°еҸ®еҳұе§җеҰ№дҝ©иҰҒжҠҠжҲҝй—Ёе…ізҙ§пјҢжҸ’дёҠй—Ёж “гҖӮе§җеҰ№зқЎеҗҺ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и·ҹзқҖжҙ—дәҶи„ҡеҲ°е ӮеұӢеҗҺйқўзҡ„еҚ§е®ӨзқЎзһҢзқЎеҺ»дәҶгҖӮиҰҒе®ўдәә们иҝҳзғӨе“ҲзҒ«пјҢиҝҳеҸ«иҙӨзҲ·з»ҷе®ўдәә зғ§жҙ—и„ҡж°ҙгҖӮиҙӨзҲ·жҠҠзӮҠеЈ¶иЈ…ж»Ўж°ҙпјҢжҢӮеңЁжўӯзӯ’й’©дёҠпјҢзҒ«иӢ—дёҖдёӘеҠІең°зӣҙеҶІзӮҠеЈ¶еә•йғЁгҖӮ
и’Ӣе©Ҷе©ҶзқЎеңЁеәҠдёҠпјҢеҝғйҮҢдёҖзӮ№д№ҹдёҚиёҸе®һпјҢй»‘еӨңдёӯпјҢеұӢйҮҢжқҘдәҶдёүдёӘдёҚйҖҹд№Ӣе®ўпјҢиҖҒжӢ…еҝғеҸ‘з”ҹд»Җд№ҲдәӢпјҢжңүдёӘд»Җд№Ҳдёүй•ҝдёӨзҹӯ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и¶Ҡжғіи¶Ҡе®іжҖ•пјҢеҘ№жҠҠиЎЈжңҚеҪ“жһ•еӨҙпјҢж”ҘеңЁжүӢдёӯпјҢдҫ§иҖіз»Ҷеҗ¬иҙӨзҲ·е’ҢдёүдёӘдәәзҡ„еҜ№иҜқгҖӮ
зҒ«зӮүеқ‘зҡ„жҹҙзҒ«иҝҳеңЁзҶҠзҶҠзҮғзғ§пјҢж—¶дёҚж—¶еҸ‘еҮәеҷје•Әзҡ„зӮёеЈ°пјҢзӮҠеЈ¶йҮҢзҡ„жҙ—и„ҡж°ҙжү“зқҖзҝ»ж»ҡгҖӮвҖңиҖҒжқҝпјҢи®ӨиҜҶжҲ‘们дёҚ?вҖқзјәйј»еӯҗй—®йҒ“гҖӮвҖңеҘҪеғҸи®ӨиҜҶжӮЁе„ҝ们пјҢжҳҜдёҚжҳҜеңЁе“Әи§ҒиҝҮ?вҖқиҙӨзҲ·зӯ”еҲ°гҖӮвҖңжҒӯе–ңдҪ пјҢиҖҒжқҝ!вҖқйј“зңјзқӣеёҰзқҖйҳҙеҶ·зҡ„йқўеӯ”гҖӮвҖңжҒӯе–ңжҲ‘д»Җд№Ҳ?вҖқиҙӨзҲ·иҝ·жғ‘дёҚи§ЈгҖӮвҖңжҒӯе–ңдҪ еұӢйҮҢеҸ‘ж°ҙе“’!вҖқйқ’зӯӢзҡ®з¬‘иӮүдёҚ笑ең°зӣҜзқҖиҙӨзҲ·гҖӮвҖңд»Җд№ҲжҲ‘еұӢйҮҢеҸ‘ж°ҙе“’пјҢеӨ–йқўеҸӘдёӢе°ҸйӣЁе•ҠпјҹвҖқиҙӨзҲ·еҝғжғіе…ҶеӨҙдёҚеҘҪпјҢйҒҮеҲ°еӨ§йә»зғҰдәҶгҖӮвҖңдёҚи®ёеҠЁпјҒвҖқзјәйј»еӯҗжү‘еҗ‘иҙӨзҲ·пјҢдёҖжҠҠжҠұдҪҸеқҗеңЁжңЁжӨ…дёҠзҡ„иҙӨзҲ·пјҢйқ’зӯӢе’Ңйј“зңјзқӣиҝ…з–ҫжӢҪдҪҸиҙӨзҲ·зҡ„е·ҰеҸіжүӢпјҢиҙӨзҲ·зҡ„еҸҢжүӢиў«еҸҚиғҢеңЁиғҢеҗҺгҖӮвҖңдҪ 们жғіе№Ід»Җд№ҲпјҹвҖқиҙӨзҲ·еӨ§еЈ°е–ҠеҲ°пјҢеҘӢеҠӣеҸҚжҠ—пјҢдёҖи„ҡжҠҠжӨ…еӯҗиёўеҗ‘з©әдёӯпјҢиҝӣиЎҢдәҶйЎҪејәжҢЈжүҺгҖӮвҖңжҲ‘们жғіжҗһзӮ№иҙ§пјҢдҪ з»ҷиҖҒеӯҗ们иҖҒе®һзӮ№!вҖқйј“зңјзқӣеӨ§еЈ°еҗјйҒ“гҖӮвҖңжҠҠз»іеӯҗжӢҝжқҘпјҢжҚҶз»‘иө·!вҖқйқ’зӯӢеҮ¶зҘһжҒ¶з…һпјҢзјәйј»еӯҗзҒ«йҖҹзҡ„д»ҺиғҢзҜ“жӢҝеҮәз»ізҙўпјҢдёүдәәжҠҠиҙӨзҲ·дә”иҠұеӨ§з»‘пјҢжүӢи„ҡиў«жҚҶеҫ—з»“з»“е®һе®һпјҢиҙӨзҲ·з–јз—ӣйҡҫеҝҚпјҢжүӢи…ҝйғҪиў«еӢ’еҮәж·ұж·ұзҡ„иӮүж§ҪгҖӮвҖңдёҚи®ёеӨ§й—№еӨ§е–ҠпјҢдёҚ然иҖҒеӯҗ们иҰҒдҪ зҡ„е°Ҹе‘ҪпјҒвҖқйј“зңјзқӣзҡ„зңјзҸ еҝ«жҺүеҮәзңјзң¶пјҢжӢҝзқҖз ҚеҲҖжһ¶еңЁиҙӨзҲ·зҡ„и„–еӯҗдёҠгҖӮзңӢеҲ°жҳҺжҷғжҷғзҡ„з ҚеҲҖпјҢиҙӨзҲ·д№ҹеҸӘеҘҪеҗ¬еӨ©з”ұе‘ҪдәҶпјҢдёҚеҶҚе–ҠеҸ«гҖӮдёүдәәжҠҠиҙӨзҲ·жӢ–еҲ°е ӮеұӢеҪ“дёӯпјҢз”ЁеҠӣж”ҫеҖ’еңЁжӯЈдёӯй—ҙзҡ„жҘјжқҝдёҠпјҢйқўйғЁеҗ‘дёӢпјҢзҙ§иҙҙжңЁең°жқҝгҖӮдёүдәәзҡ„жүӢжі•жһҒдёәйә»еҲ©пјҢдёҖзңӢйғҪжҳҜиҒҢдёҡиҖҒжүӢгҖӮ
вҖңжӢҗе“’!иҝҷе°ұжӢҗе“’!жҠўзҠҜ!ејәзӣ—!вҖқеҗ¬еҲ°е–ҠеЈ°гҖҒеҗјеЈ°гҖҒиҫұйӘӮеЈ°гҖҒжҗҸеҮ»жү“ж–—еЈ°пјҢйҳөд»—и¶ҠжқҘи¶ҠеӨ§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еҝғйҮҢжһҒеәҰзҙ§еј пјҢеҝғйҮҢе’ҡе’ҡзӣҙи·іпјҢз«ӢеҲ»иө·иә«пјҢжҠ“зқҖиЎЈжңҚиЈӨеӯҗпјҢжғҠж…Ңи·‘еҮәеҗҺй—ЁпјҢй»‘й»ўй»ўзҡ„еӨңпјҢж‘ёзқҖй»‘жҡ—иәІиҝӣеұӢеҗҺзҡ„ж ‘жһ—йҮҢ пјҢеҸҲзҲ¬еҲ°дёҖдёӘзҶҹжӮүиҖҢйҡҗи”Ҫзҡ„е°ҸеІ©еұӢи—ҸдәҶиө·жқҘпјҢдёҖиҫ№еҗ¬зқҖеҠЁйқҷпјҢдёҖиҫ№еҝ«йҖҹз©ҝдёҠиЎЈиЈӨгҖӮи’Ӣе©ҶеңЁеІ©еұӢжҖҘеҫ—и·әи„ҡпјҢдёәиҙӨзҲ·зҡ„жҖ§е‘Ҫз„ҰжҖҘпјҢдёәе…ғиӢұгҖҒе…ғз”ҹе§җеҰ№зҡ„еӨ„еўғе’ҢеҚұйҷ©жӢ…еҝ§пјҢеҸҲдёҚзҹҘжүҖжҺӘгҖӮ
еҗ¬еҲ°жү“ж–—еЈ°пјҢеҸ«е–ҠеЈ°пјҢе…ғиӢұгҖҒе…ғз”ҹе§җеҰ№жӣҙеҠ жғҠжҒҗпјҢ вҖңеҰ№еҰ№пјҢеҝ«и·‘!вҖқе…ғиӢұжҖҘдҝғзҡ„е–ҠеҲ°гҖӮе…ғз”ҹеј№ејҖй“әзӣ–пјҢд»Җд№ҲйғҪйЎҫдёҚеҫ—дәҶпјҢжІЎжңүз©ҝиЎЈзҡ„ж—¶й—ҙпјҢжҜҸдёҖз§’йғҪжҖ§е‘ҪжӮ е…іпјҢиЈёиә«зӣҙеҘ”еҗҺй—Ёиҫ№пјҢжү“ејҖжңЁж “жңЁй—ЁпјҢжҠұзқҖеҗҠи„ҡжҘјзҡ„жҹұеӨҙпјҢеһӮж»‘иҖҢдёӢпјҢжғҠжңӣеӣӣе‘ЁпјҢдјёжүӢдёҚи§Ғдә”жҢҮпјҢзЁҚдҪңиҝҹз–‘пјҢеёҰзқҖжҖҘи·ізҡ„еҝғи„ҸпјҢе…ғз”ҹ并没жңүж…ҢдёҚжӢ©и·ҜпјҢиҖҢжҳҜжҖҘдёӯжңүжҷәпјҢзӣҙи§Ӯж„ҹи§үе‘ҠиҜүеҘ№пјҢеҫҖжқЁе®¶еҸ”еҸ”(з»ӘзҲ·)пјҢеҫҖжқЁе®¶еҸ”еҸ”зҡ„ж–№еҗ‘!жҜ•з«ҹжҳҜеӨ©еӨ©иө°зҡ„и·ҜпјҢе“ӘйҮҢжңүеқ—зҹіеӨҙпјҢе“ӘйҮҢжңүдёӘжІҹпјҢе“ӘйҮҢжңүдёӘеқҺпјҢзғӮзҶҹдәҺеҝғ пјҢеҚідҪҝй»‘еӨңдёӯпјҢд№ҹиғҪеёҰзқҖеҘ”и·‘зҡ„йҖҹеәҰпјҢдёҖдёӘе°‘еҘіиЈёиә«жңқз»ӘзҲ·е®¶еҘ”еҺ»!
еңЁе…ғз”ҹи·‘еҮәеҺўжҲҝеҗҺй—Ёзҡ„еҲ№йӮЈпјҢе…ғиӢұзҢӣиө·иә«пјҢжҖҘжӢҝиЎЈиЈӨпјҢи·ҹзқҖи·‘еҮәжҲҝй—ЁпјҢжҠҠиЎЈиЈӨжү”дёӢжҘјпјҢд№ҹиЈёиә«зјҳжҹұеӨҙиҖҢдёӢпјҢж‘ёиө·иЎЈиЈӨпјҢжңқеҢ…и°·з¬јй’»еҺ»пјҢйқ зқҖеҢ…и°·з¬јйҮҢзҡ„еӨ§зҹіеӨҙпјҢж°”е–ҳеҗҒеҗҒпјҢдёҖиҫ№з©ҝдёҠиЎЈиЈӨпјҢжңӣзқҖжңЁеұӢзҡ„ж–№еҗ‘пјҢеҗ¬зқҖеұӢйҮҢеҠЁйқҷпјҢдёәзҲ¶дәІзҡ„жҖ§е‘Ҫжғ¶жҒҗпјҢе‘ңе’ҪпјҢдҪҺеЈ°е“ӯжіЈгҖӮ
вҖңжқЁеҳҺ婶еЁҳ!жқЁеҳҺ婶еЁҳ!жҲ‘жҳҜе…ғз”ҹ!вҖқе…ғз”ҹж‘ёй»‘и·‘еҲ°зҰ»з»ӘзҲ·е®¶30зұійқ зҢӘжҘј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еҒңдёӢи„ҡжӯҘпјҢеӨ§еЈ°е‘је–ҠгҖӮвҖңжҖҺд№ҲеӣһдәӢ?жңүдәәиҝҷеҳҺж—¶еҖҷй«ҳеЈ°е‘је”Ө?вҖқ敬зҲ·е’Ңз»ӘзҲ·дёҖ家дәәиҝҳеңЁе…ҙиҮҙеҚҒи¶ізҡ„жө·иҒҠпјҢзӘҒ然еҗ¬еҲ°жҖҘдҝғзҡ„е‘је”ӨпјҢйЎҝж—¶иӯҰи§үиө·жқҘгҖӮвҖңжқЁеҳҺ婶еЁҳпјҢжқЁеҳҺ婶еЁҳпјҢжӮЁе„ҝеҝ«жқҘдёҖе“ҲпјҢеҸ«жқЁеҳҺеҸ”еҸ”иҺ«жқҘпјҢжқЁеҳҺеҸ”еҸ”еҚғдёҮиҺ«жқҘ!вҖқжқЁеҳҺ婶еЁҳе°ұжҳҜеҗҙе©Ҷе©ҶпјҢеӨ§е®¶дёҖж—¶ж‘ёеӨҙдёҚзҹҘи„‘пјҢдёҚзҹҘе…ғз”ҹжңүд»Җд№ҲдәӢпјҢжӣҙдёҚзҹҘеҸ‘з”ҹдәҶд»Җд№ҲдәӢгҖӮз»ӘзҲ·еҸ«еҗҙе©Ҷе©ҶиҝһеҝҷеҮәеҺ»зңӢзңӢпјҢеҗҙе©Ҷе©ҶзӮ№зҮғж ‘зҡ®зҒ«жҠҠпјҢжқҘеҲ°е…ғз”ҹиә«иҫ№пјҢзңӢеҲ°е…ғз”ҹе…үзқҖиә«еӯҗпјҢеӨ§еҗғдёҖжғҠ!вҖңжҲ‘家жқҘжҠўзҠҜе“’пјҢжӯЈеңЁеұӢйҮҢжҠўдёңиҘҝпјҢжҲ‘зҲ№жҳҜжӯ»жҳҜжҙ»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!жҲ‘жҳҜд»Һй“әдёҠзјҳеҗҠи„ҡжҘјжҹұеӨҙпјҢж»‘дёӢжқҘпјҢи·‘иҝҮжқҘзҡ„пјҢжІЎз©ҝиЎЈжңҚ!вҖқе…ғз”ҹеӨ§е“ӯиө·жқҘгҖӮвҖңдҪ иҺ«жҖҘпјҢдҪ иҺ«е“ӯпјҢжҲ‘马дёҠз»ҷдҪ жүҫиЎЈжңҚпјҢдҪ зӯүе“ҲгҖӮвҖқеҗҙе©Ҷиҝһеҝҷи·‘еҲ°еұӢйҮҢпјҢжҠҠзңӢеҲ°зҡ„жғ…еҶөе‘ҠиҜүдәҶз»ӘзҲ·е’Ң敬дёҡгҖӮвҖңжғ…еҶөеҚұжңәпјҢжҲ‘们дёҚиғҪи§Ғжӯ»дёҚж•‘!вҖқпјҢ敬зҲ·жңӣзқҖз»ӘзҲ·гҖӮвҖң马дёҠз»ҷеҘ№жүҫиЎЈжңҚз©ҝдёҠпјҢеҶҚжғіеҠһжі•гҖӮвҖқз»ӘзҲ·еӮ¬дҝғеҗҙе©Ҷе©ҶгҖӮе…ғз”ҹеҝ«йҖҹз©ҝдёҠеҗҙе©ҶжүҫжқҘзҡ„иЎЈиЈӨпјҢи·ҹзқҖеҗҙе©ҶиҝӣеҲ°з»ӘзҲ·е®¶зҡ„е ӮеұӢпјҢи„ёдёҠдёҚеҒңең°жөҒзқҖзңјжіӘпјҢдёҖиҫ№з”ЁиЎЈиў–дёҚеҒңең°ж“ҰгҖӮжҠҠ家йҮҢйҒӯдәҶдёүдёӘжҠўзҠҜзҡ„жғ…еҶөз»ҷз»ӘзҲ·е’Ң敬зҲ·еҝ«иҝ°дәҶдёҖйҒҚгҖӮиҜҙе®ҢпјҢеҷ—йҖҡдёҖеЈ°пјҢе…ғз”ҹи·ӘеҖ’еңЁз»ӘзҲ·е’Ң敬зҲ·йқўеүҚгҖӮзңӢеҲ°е…ғз”ҹдёӢи·ӘпјҢеҮ дёӘеӯ©еӯҗд№ҹеӣҙдәҶиҝҮжқҘгҖӮвҖңиө·жқҘпјҢиө·жқҘпјҢе…ғз”ҹиө·жқҘпјҢжҲ‘们马дёҠжғіеҠһжі•ж•‘дҪ зҲ¶дәІгҖҒжҜҚдәІе’Ңе§җе§җгҖӮвҖқ敬зҲ·иҰҒеҗҙе©Ҷе©ҶжҠҠе…ғз”ҹжү¶иө·жқҘгҖӮвҖңе…ғз”ҹ家йҒӯеҠ«пјҢдёүдёӘйҮҺиӣ®зҡ„жҠўзҠҜжӯЈеңЁе®һж–ҪжҠўеҠ«пјҢй»„е“ҘеҸҲдёҚеңЁе®¶пјҢи’Ӣе©Ҷе©Ҷе’Ңе…ғиӢұзҡ„жғ…еҶөд№ҹдёҚзҹҘйҒ“пјҢжҲ‘们еҸӘжңүдёӨдёӘеӨ§зҲ·е®¶пјҢе®қзҲ·зҡ„家зҰ»иҝҷеҸҲзЁҚиҝңпјҢе–Ҡд»–ж—¶й—ҙжқҘдёҚеҸҠпјҢжҖҺд№ҲеҠһ?вҖқз»ӘзҲ·жңӣзқҖ敬зҲ·гҖӮвҖңзЎ¬жқҘдёҚеҸҜеҸ–пјҢжӯЈйқўдәӨй”ӢпјҢжҲ‘们еӨ„дәҺејұеҠҝпјҢзӢ—жҖҘи·іеўҷпјҢејәзӣ—иӢҘиў«йҖјжҖҘдәҶпјҢжІЎжңүдәҶйҖҖи·ҜпјҢжҳҜдјҡеҠЁжқҖжңәж»ҙгҖӮвҖқ敬зҲ·жңәжҷәзҡ„иҜҙйҒ“гҖӮвҖңеҜ№пјҢжҷәеҸ–пјҢеҲ°еә•дҪ и„‘еЈізҒөе…үгҖӮвҖқз»ӘзҲ·зңјеүҚдёҖдә®пјҢеҜ№ж•¬зҲ·зӮ№иөһгҖӮвҖңжү“йҖҖдёҚеҰӮеҗ“йҖҖпјҢиҝҷж ·пјҢжҲ‘е’Ңз»Әе“ҘжӢҝжҢ–й”„пјҢи–…й”„пјҢд»ҺдёӢйқўеӨ§и·Ҝйқ иҝ‘е…ғз”ҹ家пјҢе«Ӯеӯҗе’Ңе…ғз”ҹжӢҝз ӮеҲҖгҖҒй•°еҲҖпјҢеӯ©еӯҗ们жүӢйҮҢжӢҝж №жңЁжЈҚпјҢе«Ӯеӯҗе’Ңе…ғз”ҹеёҰеӯ©еӯҗ们д»ҺдёҠйқўзҡ„е°Ҹи·Ҝйқ иҝ‘пјҢеҪўжҲҗдёҠдёӢеҢ…жҠ„зҡ„жҖҒеҠҝпјҢеҝ«еҲ°е…ғз”ҹ家зҡ„еұӢиҫ№ж—¶пјҢеӨ§е®¶еҗҢж—¶еӨ§е–Ҡ:жҚүејәзӣ—е•ҰпјҢжҠ“жҠўзҠҜе•ҰпјҢжҚүеҲ°иө·пјҢжҠ“еҲ°иө·!еЈ°йҹіи¶ҠеӨ§и¶Ҡй«ҳи¶ҠеӨҡи¶ҠеҘҪпјҢеӨ§е®¶жіЁж„ҸиҮӘе·ұе®үе…ЁпјҢе«Ӯеӯҗе’Ңе…ғз”ҹиҝҳиҰҒжіЁж„Ҹеӯ©еӯҗ们зҡ„е®үе…ЁгҖӮвҖқз»ӘзҲ·еҝ«йҖҹжүҫжқҘжқүжңЁзҡ®пјҢеҒҡжҲҗдёӨжҠҠзҒ«жҠҠпјҢзӮ№зҮғгҖӮвҖңеҮәеҸ‘!вҖқз»ӘзҲ·дёҖеЈ°д»ӨдёӢпјҢй»‘еӨңйҮҢпјҢеңЁжһ—дёӯеұұи·ҜпјҢе…өеҲҶдёӨи·ҜпјҢжү“зқҖзҒ«жҠҠпјҢжӢҝзқҖжҢ–й”„пјҢз ҚеҲҖпјҢеҗ‘иҙӨзҲ·е®¶йҖјиҝ‘гҖӮеҰӮжһңдҪ жҳҜдёҖдёӘжҮҰеӨ«пјҢи§Ғжӯ»дёҚж•‘пјҢзңјзқҒзқҒзңӢзқҖеҸ—е®іиҖ…иө°еҗ‘жӣҙж·ұзҡ„зҒҫйҡҫпјҢдҪ зҡ„иүҜеҝғе°ұиў«зӢ—еҗғдәҶпјӣеҰӮжһңдҪ жҳҜдёҖдёӘејәиҖ…пјҢе°ұиҰҒжӢҝиө·жӯҰеҷЁпјҢиө¶иө°ејәзӣ—е’Ңдҫөз•ҘиҖ…гҖӮ
иҙӨзҲ·е®¶йҮҢпјҢиҙӨзҲ·иў«з»‘пјҢејәзӣ—жЁӘиЎҢгҖӮиҙӨзҲ·йқўйғЁжңқдёӢпјҢи¶ҙеңЁе ӮеұӢжӯЈдёӯпјҢеҸҢжүӢеҸҚиғҢдәҺеҗҺпјҢеҸҢи…ҝиў«жҚҶз»‘пјҢж— жі•еҠЁеј№пјҢеғҸдёӘеғөе°ёпјҢеҳҙйҮҢеҸ‘еҮәз—ӣиӢҰзҡ„е‘»еҗҹпјҢвҖңиҝҷеӣһжҲ‘еҸӘжҖ•иҰҒжӯ»еңЁејәзӣ—жүӢйҮҢпјҢжҠўдәҶдёңиҘҝд№ҹе°ұз®—дәҶпјҢдёүдёӘзӢ—ж—Ҙж»ҙиҜҙдёҚе®ҡиҝҳдјҡжҠҠжҲ‘жқҖжҺүвҖҰвҖҰвҖқиҙӨзҲ·и¶Ҡжғіи¶ҠжғҠжғ§гҖӮ
дёүдёӘжҠўзҠҜеӨ§еұ•жӢіи„ҡпјҢз•…иЎҢж— йҳ»пјҢеҰӮе…Ҙж— дәәд№ӢеўғпјҢеӨ§зҒҜеӨ§дә®ж»ЎеұӢжҗңжҹҘпјҢеҰӮйҮҺзӢ—зҡ„е—…и§үпјҢзҝ»йҒҚжҜҸдёҖдёӘи§’иҗҪпјҢз ёејҖжҜҸдёҖеҸЈжҹңеӯҗпјҢж’¬ејҖжҜҸдёҖеҸЈз®ұеӯҗгҖӮйқ’зӯӢдёҖи„ҡиёўејҖеҗҠи„ҡжҘјдёҠзҡ„еҺўжҲҝпјҢејҖе§Ӣзҝ»з®ұеҖ’жҹңгҖӮйј“зңјзқӣдёҖи„ҡ蹬ејҖи’Ӣе©ҶеҚ§жҲҝпјҢз ёејҖжҹңеӯҗпјҢеҝғдёӯзӘғе–ңпјҢеҝҚдёҚдҪҸвҖңе“Ҳе“Ҳе“ҲвҖқзӢӮ笑иө·жқҘпјҢеҮ дёӘзҷҪиҠұиҠұзҡ„иўҒеӨ§еӨҙпјҢеҮ дёӘз”ҹй”Ҳзҡ„й“ңеЈіеӯҗпјҢеЎһиҝӣдәҶд»–зҡ„еҸЈиўӢгҖӮзјәйј»еӯҗжҗӯзқҖжӨ…еӯҗпјҢй«ҳй«ҳз«ҷеңЁжӨ…еӯҗдёҠпјҢд»ҺзҒ«зӮүеқ‘дёҠж–№зҡ„зӮ•жһ¶дёҠпјҢеҸ–дёӢдёҖеқ—еқ—й•ҝж»ЎзҷҪйңүзҡ„иҖҒи…ҠиӮүпјҢиҙӘе©Әең°жөҒзқҖж¶Һж°ҙпјҢеҸЈдёӯеҝөеҝөжңүиҜҚ:еҘҪ家дјҷпјҢеҘҪ家дјҷ!дёҖиҫ№жҠҠиҖҒи…ҠиӮүеҫҖиғҢзҜ“йҮҢжҸ’гҖӮйқ’зӯӢжҠҠеҺўжҲҝзҝ»дәҶдёӘеә•жңқеӨ©пјҢиҝҳжІЎзҝ»еҲ°еҖјй’ұзҡ„зү©е“ҒпјҢеҫҲдёҚз”ҳеҝғпјҢеҸҲжҠҠеәҠдёҠзҡ„й“әзӣ–жЈүзө®дёҖ件дёҖ件жҺҖејҖпјҢжү”еҲ°ең°жқҝдёҠпјҢеҘҪ家дјҷ!еәҠдёҠиҚүеһ«йҮҢйңІеҮәдёҖеүҜй—Әе…үзҡ„银иҖізҺҜпјҢйқ’зӯӢжҚҸеңЁжүӢйҮҢпјҢиҙӘе©Әзҡ„еҘёз¬‘пјҢйә»еҲ©зҡ„иЈ…иҝӣиЎЈе…ңйҮҢгҖӮиҝҷеҜ№й“¶иҖізҺҜиҝҳжҳҜй»„е“Ҙз»ҷе…ғиӢұд№°зҡ„е®ҡжғ…зү©гҖӮ
з»ӘзҲ·е’Ң敬зҲ·дёҫзқҖзҒ«жҠҠпјҢжӢҝзқҖ家дјҷпјҢзҒ«йҖҹиЎҢиҝӣеҲ°зҰ»иҙӨзҲ·е®¶еҗҠи„ҡжҘј40зұізҡ„ең°ж–№пјҢж—¶й—ҙе°ұжҳҜз”ҹе‘Ҫ!й«ҳеЈ°еӨ§е–ҠвҖңжҚүејәзӣ—е•ҠвҖҰвҖҰжҠ“ејәзӣ—е•ҠвҖҰвҖҰвҖқвҖңжҚүеҲ°иө·пјҢжҚүеҲ°иө·вҖҰвҖҰвҖқеҗҙе©Ҷе’Ңе…ғз”ҹиҝҳжңүеӯ©еӯҗ们еңЁдёҠйқўзҡ„е°Ҹи·Ҝй«ҳеЈ°еӣһеә”гҖӮеҗ¬еҲ°иө¶жҠўзҠҜзҡ„е–ҠеЈ°пјҢи’Ӣе©Ҷе’Ңе…ғиӢұжҸҗзқҖзҡ„еҝғи„ҸпјҢзЁҚжқҫдәҶдёҖдәӣпјҢвҖңжңүж•‘дәҶпјҢжңүж•‘дәҶ!вҖқзә·зә·д»ҺеІ©еұӢе’ҢеҢ…и°·з¬јйҮҢй’»еҮәжқҘпјҢе°–еЈ°й«ҳе–ҠпјҢвҖңжҠ“ејәзӣ—е•ҠпјҢжҚүејәзӣ—е•ҠпјҒвҖқдёҖж—¶й—ҙжҠ“ејәзӣ—зҡ„е–ҠеЈ°е“ҚеҪ»е®ҳеә„жІіи°·пјҢз©ҝйӣҫз ҙдә‘пјҢйңҮиҚЎеңЁеңҹе ЎдёҠз©әгҖӮ
еҸӘеҗ¬еҫ—иҙӨзҲ·еұӢйҮҢ пјҢжҘјжқҝйғҪеҝ«йңҮж–ӯпјҢеҗ¬еҲ°зӘҒеҰӮе…¶жқҘең°жҚүжӢҝе–ҠеЈ°пјҢдёүдёӘжҠўзҠҜеӨ§йӘҮпјҢд»“зҡҮеҘ”йҖғгҖӮвҖңйҒӯиҗҪ!йҒӯиҗҪ!дјҷ计们пјҢйҖғе‘Ҫе•ҰпјҢйҖғе‘Ҫе•Ұ!вҖқзјәйј»еӯҗд»ҺжӨ…еӯҗдёҠйЈһдёӢжқҘпјҢдёӨжӯҘеҘ”еҮәе ӮеұӢпјҢжңқдёңиҫ№жқҘи·ҜвҖ”вҖ”зҹ®зүҷеӯҗгҖҒж°ҙдә•иәәж–№еҗ‘йҖғеҺ»пјҢдёҖиҫ№еңЁеүҚйқўе–ҠвҖңдјҷ计们пјҢйҖғе‘Ҫе•ҰвҖқгҖӮйј“зңјзқӣдә”жӯҘ并еҒҡдёӨжӯҘпјҢд»Һе ӮеұӢеҗҺзҡ„еҚ§е®ӨжғҠжҒҗйҖғеҮәпјҢзҙ§и·ҹзјәйј»еӯҗгҖӮйқ’зӯӢд»ҺеҺўжҲҝжғҠж…Ңи·‘еҮәпјҢиў«й—ЁеқҺз»ҠеҲ°пјҢвҖңе’ҡвҖқзҡ„дёҖеЈ°пјҢйҮҚйҮҚж‘”еҖ’еңЁе ӮеұӢпјҢдёҖеЈ°е“Һе“ҹе°–еҸ«пјҢеҸҲзҢӣең°зҲ¬иө·жқҘпјҢдёӨжӯҘеҘ”еҮәе ӮеұӢпјҢжӢје‘ҪйҖғзӘңпјҢзҙ§иҝҪйј“зңјзқӣиҖҢеҺ»гҖӮ
вҖңжҠўзҠҜи·‘дәҶвҖҰвҖҰжҠўзҠҜи·‘дәҶвҖҰвҖҰеҝ«жқҘдәәе•ҠпјҢеҝ«жқҘдәәе•ҠвҖҰвҖҰвҖқиҙӨзҲ·з”ЁеҠӣзҝ»иҝҮиә«еӯҗпјҢжҶӢзқҖиғёи…”пјҢз”ЁеҠӣе–ҠеҲ°пјҢдјјеҸҲдёҚиғҪе®Ңе…Ёеҗҗзәіиғёдёӯзҡ„ж°”жөҒпјҢжңүеҠӣдҪҝдёҚдёҠгҖӮ
вҖңжҚүејәзӣ—е•ҠпјҢжҠ“жҠўзҠҜе•Ҡ вҖқвҖңжҚүеҲ°иө·пјҢжҠ“еҲ°иө·зҡ„вҖқзҡ„е–ҠеЈ°пјҢиҝҳеңЁжӯӨиө·еҪјдјҸпјҢеұұи°·еӣһиҚЎгҖӮеӨ§е®¶жӢҝзқҖ家дјҷзә·зә·еҗ‘иҙӨзҲ·е®¶йқ иҝ‘гҖӮ
з»ӘзҲ·е’Ң敬дёҡиө¶еҲ°иҙӨзҲ·е®¶йҮҢпјҢеҸӘи§ҒиҙӨзҲ·йқўеҰӮеңҹиүІпјҢзӘҳеўғе’ҢдёҚе Әе‘ҲзҺ°еңЁзңјеүҚпјҢи·ҹжӯ»дәҶдёҖж¬Ўж— ејӮпјҢз»ӘзҲ·иҝ…з–ҫз”Ёй•°еҲҖеё®иҙӨзҲ·еүІејҖз»ізҙўпјҢи§ЈйҷӨжҚҶз»‘гҖӮиҙӨзҲ·жө‘иә«иў«еӢ’еҮәж·ұж·ұзҡ„иӮүж§ҪпјҢеӢ’еҮәж·ұеҮ№зҡ„жҡ—зәўиүІпјҢж·ӨиЎҖж»Ўиә«гҖӮеӣӣиӮўйә»жңЁпјҢдёҖж—¶дёҚиғҪз«ҷз«ӢпјҢеӢүејәеқҗдәҶиө·жқҘпјҢвҖңдёӨдҪҚе…„ејҹиҲҚиә«зӣёж•‘пјҢз»Ҳз”ҹдёҚеҝҳпјҢжҒ©жғ…й“ӯи®°дёҖз”ҹ!вҖқ并з»ҷ敬зҲ·е’Ңз»ӘзҲ·еҒҡзЈ•еӨҙзҠ¶гҖӮз»ӘзҲ·е’Ң敬зҲ·еҸҲеё®иҙӨзҲ·жҺЁгҖҒжҠ№гҖҒжҠҡгҖҒжҚҸж»Ўиә«зҡ„иЎҖз—•пјҢз»ӘзҲ·ж…ўж…ўжҒўеӨҚзҹҘи§үгҖӮжӯӨеҲ»пјҢеҗҙе©ҶпјҢе…ғз”ҹпјҢе…ғиӢұпјҢи’Ӣе©ҶпјҢеӯ©еӯҗ们д№ҹзә·зә·иө¶еҲ°еұӢйҮҢгҖӮ
зңӢеҲ°иҙӨзҲ·еғөзЎ¬ең°еқҗеңЁе ӮеұӢеҪ“дёӯпјҢиҗҪйӯ„жғҠйӯӮзҡ„иӢҚзҷҪи„ёиүІпјҢ家йҮҢйҒӯжӯӨеҠ«йҡҫпјҢи’Ӣе©ҶгҖҒе…ғиӢұгҖҒе…ғз”ҹжіӘжөҒдёҚжӯўгҖӮеҗҙе©Ҷе©Ҷе®үж…°йҒ“вҖңиө¶и·‘дәҶејәзӣ—пјҢдёҖ家дәәе№іе®үе°ұеҘҪпјҢе№іе®үе°ұеҘҪ!вҖқгҖӮвҖңжҳҜзҡ„пјҢдёҚиҰҒе“ӯжіЈдәҶпјҢиө¶еҝ«жҢҜдҪңзІҫзҘһпјҢжҲ‘们任еҠЎиҝҳжІЎе®ҢжҲҗпјҢд»ҠеӨңжҲ‘们没жңүеҝғжғ…дј‘жҒҜпјҢд№ҹж— жі•дј‘жҒҜпјҢжҲ‘们иҰҒжҠҠжҠўзҠҜиө¶еҮәеңҹе ЎпјҢиө¶еҮәжҙһжәӘеқӘ!вҖқз»ӘзҲ·жһңж–ӯең°еҒҡеҮәеҶіе®ҡгҖӮвҖңжҳҜзҡ„пјҢжҲ‘们иҰҒ继з»ӯй©ұиө¶ејәзӣ—пјҢе®ңе°Ҷеү©еӢҮиҝҪз©·еҜҮ!вҖқ敬зҲ·еқҡе®ҡең°иҜҙйҒ“гҖӮвҖңжҲ‘иҰҒеҺ»иө¶пјҢиҖҒеӯҗиҰҒеҺ»жқҖдәҶ他们!вҖқиҙӨзҲ·жёҗжёҗжҒўеӨҚзҹҘи§үпјҢж…ўж…ўз«ҷдәҶиө·жқҘпјҢжү“дәҶдёҖдёӘ趔趄гҖӮ
з»ӘзҲ·гҖҒ敬зҲ·е’ҢиҙӨзҲ·пјҢдёүдәәд»”з»ҶжҹҘзңӢдәҶжҜҸдёӘжҲҝй—ҙзҡ„жғ…еҪўпјҢеұӢйҮҢеҲ°еӨ„дёҖзүҮзӢји—үгҖӮиғҢзҜ“йҮҢзҡ„иҖҒи…ҠиӮүеҺҹе°ҒдёҚеҠЁпјҢиЈ…еңЁиғҢзҜ“йҮҢгҖӮејәзӣ—зҡ„дёүдёӘиғҢзҜ“пјҢдҪңдёәжҠ—еҮ»дҫөз•ҘиҖ…зҡ„и§ҒиҜҒпјҢе…ЁйғЁз•ҷеңЁдәҶиҙӨзҲ·е®¶гҖӮеҪ“然пјҢиҝҳжңүж„ҸжғідёҚеҲ°зҡ„收иҺ·пјҢжҠўзҠҜиғҢзҜ“йҮҢз•ҷдёӢдәҶдёүеҢ№йқ’иүІзҡ„еңҹеёғ!
дёүдёӘз”·дәәеҶҚж¬ЎеҸ‘иө·дәҶеҶІй”ӢпјҢеҠ ејәдәҶзҒ«жҠҠ пјҢеҸ®еҳұеҗҙе©ҶгҖҒи’Ӣе©ҶгҖҒе…ғиӢұгҖҒе…ғз”ҹз•ҷеңЁеұӢйҮҢпјҢдёҖиө·ж”¶жӢҫж•ҙзҗҶеұӢйҮҢзҡ„зӢји—үгҖӮдёүдёӘзӘҒеҮ»жүӢжү“зқҖзҒ«жҠҠпјҢжӢҝзқҖз ҚеҲҖпјҢдёҖи·Ҝеҗ‘зҹ®зүҷеӯҗгҖҒж°ҙдә•иәәж–№еҗ‘иҝҪеҺ»пјҢдёҖиҫ№й«ҳе–ҠпјҢвҖңжҚүжҠўзҠҜе•ҰпјҢжҠ“ејәзӣ—е•ҠвҖқпјҢдёҖзӣҙиҝҪеҲ°ж°ҙдә•иәәдёҠйқўзҡ„еұұжўҒгҖӮе–ҠеЈ°йЈҳеңЁйҷҲ家еҜЁеұұжўҒпјҢеӣһиҚЎеңЁйә»еқ‘е’Ңж—Ұ家еқЎжІіи°·гҖӮйӮЈеҮ дёӘең°ж–№зҡ„дҪҸжҲ·зә·зә·иө°еҮәеұӢйҮҢпјҢжӢҝиө·жӯҰеҷЁпјҢй«ҳеәҰиӯҰжғ•пјҢйҡҸж—¶еә”жҲҳжқҘзҠҜд№ӢиҙјгҖӮ
иө¶ејәзӣ—гҖҒжҚүжҠўзҠҜзҡ„йңҮиҚЎеЈ°пјҢдј еҲ°дәҶе®қзҲ·е®¶йҮҢпјҢе®қзҲ·еёҰйўҶеј е©Ҷе©Ҷе’Ңеӯ©еӯҗ们жү“зқҖзҒ«жҠҠзҒ«йҖҹиө¶жқҘпјҢеҸӮдёҺжҸҙж•‘гҖӮ
з»ӘзҲ·гҖҒ敬зҲ·гҖҒиҙӨзҲ·зҙ§иҝҪеҲ°ж°ҙдә•иәәеұұи„ҠпјҢжІҝи·Ҝиҝ”еӣһгҖӮйӮЈдёҖеӨңпјҢеӣӣжқЎжұүеӯҗжҗңжҹҘдәҶйҷ„иҝ‘жүҖжңүзҡ„е°Ҹи·ҜпјҢеҸҲзҷ»дёҠиҖҒеЁғеҜЁпјҢеҜ№зқҖжҙһжәӘеқӘй«ҳеЈ°еӨ§е–Ҡ:д№ЎдәІд»¬пјҢжқҘејәзӣ—е•ҰвҖҰвҖҰд№ЎдәІд»¬йғҪиө·жқҘиө¶ејәзӣ—е•ҠвҖҰвҖҰжҙһжәӘеқӘ家家жҲ·жҲ·пјҢзҒҜз¬јзҒ«жҠҠпјҢеұӢеүҚеұӢеҗҺпјҢеңЁжҜҸдёҖжқЎи·ҜдёҠпјҢзҒ«е…үз…§еҪ»еӨңз©әпјҢеұ•ејҖең°ж‘ҠејҸжҗңжҹҘпјҢеҪ»еә•йңҮж…‘дәҶејәзӣ—гҖӮ
йӮЈдёҖеӨң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жғҠжҒҗд№ӢеӨң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дёҚзң д№ӢеӨңпјҢжҳҜдёҖдёӘжӯЈд№үд№ӢеӨңгҖӮ
иө¶иө°ејәзӣ—еҗҺпјҢеңҹе ЎеҸҲжҒўеӨҚдәҶеҫҖж—Ҙзҡ„е®ҒйқҷгҖӮ
ж— е·§дёҚжҲҗд№ҰгҖӮиҮӘд»ҺиҙӨзҲ·е®¶йҒӯејәзӣ—жү“еҠ«еҗҺпјҢ家иҝҗдёҚжөҺпјҢдёҖзӣҙиө°дёӢеқЎи·ҜгҖӮеңЁеҗҺжқҘзҡ„ж—¶д»ЈиҝӣзЁӢе’Ңж”ҝжІ»иҝҗеҠЁдёӯпјҢиҙӨзҲ·е®¶дёҖеәҰиў«еҲ’дёәеҜҢеҶң пјҢеҗҺйҷҚдёәдёӯеҶңпјҢз»ҸеҺҶдәҶдёҖдәӣзЈЁйҡҫгҖӮ
и§Јж”ҫеҗҺпјҢе…ғз”ҹе«ҒеҫҖеӨӘе№ідёүеІ”дәҺ家пјҢеҗҺйҡҸе„ҝеӯҗе®ҡеұ…е®№зҫҺпјҢе„ҝеӯҗе»әиө·дәҶдёүеұӮе°ҸжҙӢжҲҝпјҢе®үеәҰжҷҡе№ҙгҖӮиҙӨзҲ·еҗҺжқҘйҡҸеӨ§еҘіе„ҝеҘіе©ҝе®ҡеұ…е®ЈжҒ©гҖӮжҷҡе№ҙпјҢиҙӨзҲ·и·ҹйҡҸе№Іе„ҝеӯҗдҪҸеңЁеңҹе ЎеҜ№й—Ёзҡ„жҹіжқ‘пјҢзӣҙеҲ°з»ҲиҖҒпјҢжҚ®иҜҙе№Іе„ҝеӯҗ姓жқҺгҖӮ
иҙӨзҲ·зҡ„жңЁеұӢдёҖзӣҙз•ҷеңЁеңҹе ЎпјҢеҗҲдҪңзӨҫе’Ңдәәж°‘е…¬зӨҫж—¶д»ЈпјҢжңЁжҲҝиҝҳжҳҜжҙһжәӘеқӘзҡ„зІ®йЈҹдёӯиҪ¬з«ҷе’ҢеҠіеҠЁй©ҝз«ҷгҖӮйӮЈж—¶жҙһжәӘдәәж°‘еңЁеңҹе ЎгҖҒзҹ®зүҷеӯҗз ҚжІҷпјҢзғ§жІҷпјҢеҲҖиҖ•зҒ«з§ҚпјҢжҜҸе№ҙ收иҺ·еҮ зҷҫд№Қз¬ј(жҜ”иғҢзҜ“жӣҙеӨ§зҡ„зҜҫеҷЁ)иӢһи°·пјҢе°ұе Ҷж”ҫеңЁз»ӘзҲ·з•ҷеңЁеңҹе Ўзҡ„жңЁеұӢйҮҢгҖӮжҙҫдё“дәәеҖје®ҲпјҢзӮ•е№ІеҗҺпјҢеҶҚеҲҶеҲ°е®¶е®¶жҲ·жҲ·гҖӮд»ҺйӮЈж—¶иө·пјҢжҙһжәӘдәәж°‘еҹәжң¬и§ЈеҶідәҶеҗғйҘӯзҡ„й—®йўҳпјҢдёҚеҶҚеҗғж ‘зҡ®иҚүж №гҖӮ
дёҚе№ёзҡ„жҳҜпјҢжңүдёҖе№ҙеҸ‘еӨ§ж°ҙпјҢиҙӨзҲ·е®¶зҡ„жҲҝеӯҗең°еҹәеҙ©еЎҢпјҢжҲҝеұӢеҖ’еЎҢж•Јжһ¶пјҢиҙӨзҲ·е®¶еңЁеңҹе Ўзҡ„з•ҷеӯҳж¶ҲеӨұеңЁйЈҺйӣЁзҡ„дҫөиҡҖдёӯпјҢж¶ҲеӨұеңЁиӢҚиҢ«зҡ„еұұжһ—д№ӢдёӯгҖӮ
и§Јж”ҫеҗҺпјҢз»ӘзҲ·е’Ңе®қзҲ·дёӨ家д№ҹзӣёз»§иҝҒеҮәеңҹе ЎгҖӮз»ӘзҲ·жҗ¬еҲ°ж ёжЎғејҜпјҢе®қзҲ·иҝҒеҫҖйә»еқ‘гҖӮеңЁж–°зҡ„еңҹең°дёҠпјҢ他们еӯҗеӯҷж»Ўе ӮпјҢжһқз№ҒеҸ¶иҢӮпјҢиҝҮзқҖеӢӨеҠізҡ„е№ёзҰҸз”ҹжҙ»гҖӮ
敬зҲ·еӣһеҲ°дәҶжқЁе®¶еһӯпјҢиҝҮзқҖд»–зҡ„еҶңиҖ•з”ҹжҙ»пјҢз”Ёд»–й«ҳе°ҡзҡ„дәәж јжҠҡиӮІж•ҷиӮІеӯҗеҘігҖӮ敬зҲ·е№ҙиҪ»ж—¶еҲ°еңҹе ЎдҪңе®ўпјҢи·Ҝи§ҒдёҚе№ідёҖеЈ°еҗјпјҢиҜҘеҮәжүӢж—¶е°ұеҮәжүӢпјҢд»–зҡ„йӮЈз§Қй«ҳе°ҡзІҫзҘһпјҢжҳҜеҖјеҫ—敬仰и®ҙжӯҢзҡ„гҖӮ
жңүдёҖе№ҙпјҢ敬зҲ·еҲ°е®№зҫҺдҫ„е„ҝ家дҪңе®ўпјҢе°Ҫз®ЎйӮЈж—¶е№ҙдәӢе·Ій«ҳпјҢдёғеҚҒеӨҡеІҒпјҢи°Ҳиө·еңҹе ЎеҫҖдәӢпјҢд»–дҫқ然жҸҸиҝ°зҡ„з»ҳеЈ°з»ҳиүІпјҢжғ…иҠӮи·Ңе®•иө·дјҸпјҢжүЈдәәеҝғејҰгҖӮдҫ„е„ҝе‘ҠиҜү敬зҲ·пјҢе…ғз”ҹе…ӯеҚҒеӨҡеІҒдәҶпјҢзҺ°еңЁи·ҹзқҖе„ҝеӯҗе°ұдҪҸеңЁе®№зҫҺгҖӮ敬зҲ·йЎҝж—¶жқҘдәҶзІҫзҘһпјҢйқһиҰҒдҫ„е„ҝеёҰд»–еҺ»е…ғз”ҹ家зңӢзңӢдёҚеҸҜпјҢжқҘеҲ°е…ғз”ҹ家пјҢдёҖиө·еӣһеҝҶдәҶеңҹе ЎеҫҖдәӢгҖӮ敬зҲ·е…«еҚҒеӨҡеІҒз»ҲиҖҒпјҢжҲ‘еҸӮеҠ дәҶд»–зҡ„葬зӨјгҖӮ
еңҹе ЎеҫҖдәӢзҡ„еҪ“дәӢдәәеӨ§еӨҡе·ІдҪңеҸӨпјҢжҲҗдёәдёҖж®өе°ҳе°Ғзҡ„еҫҖдәӢгҖӮжҲ‘еҸӘжғіе‘ҠиҜүеӨ§е®¶пјҢеҫҲеӨҡдәӢжғ…пјҢзңӢдјјдёҖдёӘи®©дәәдёҚи§Је…¶еӣ зҡ„з»“жһңпјҢе…¶е®һйҮҢйқўи—ҸзқҖдёҖдәӣеҒ¶з„¶пјҢд№ҹи—ҸзқҖдёҖдәӣеҝ…然пјҢдёӘдәәе‘ҪиҝҗдёҺеҺҶеҸІзҡ„иғҢжҷҜпјҢдәәзү©зҡ„жҖ§ж јпјҢдёӘдәәзҡ„иғёжҖҖд»ҘеҸҠжүҖи®ӨиҜҶдәӨеҫҖзҡ„дәәпјҢзӯүзӯүпјҢиҜёеӨҡз»јеҗҲзҡ„еӣ зҙ зӣёдәӨзј гҖӮ